高莽(1926-) 哈尔滨人,文学翻译家、作家、画家。 曾任《世界文学》主编,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艺术六十余年,在青年时代就曾经翻译过俄罗斯著名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散文诗,后来又翻译过根据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改编的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、莱蒙托夫的《假面舞会》、玛雅科夫斯基的《臭虫》等等,已出版的著作有《文人剪影》、《灵魂的归宿——俄罗斯墓园文化》、《圣山行——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》,准备出版的有《俄罗斯大师故居》、《俄罗斯美术随笔》等。 ■记者手记 “我这个人是随着命运走,命运让我怎么地,我就怎么地。”先生用极浓的东北腔对我说。 不知道为什么,东北人说起话来仿佛格外诚恳和发自肺腑,透着一股豪爽劲儿。而那些他们所独有的方言词汇更具有普通话难以言表的趣味和魅力。 但是,东北方言却一度成了先生做翻译时的障碍。年轻时的他从未离开过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伪满洲国,以为全国人民都是这么说话,翻译出来的作品也充满了东北俚语,直到一位女作家提醒他语言不纯。 有趣的是,谈话期间,先生不断地与我商量:“我做翻译真的没什么好谈的。我想,要不我们谈谈我画的画吧,那更有意思一些。”说着,就起身拿出许多画作出来给我看。 我说:“我发现您对绘画的兴趣要高于翻译啊?”先生马上点头说:“是的,是的!是命运让我做了翻译家。” 我不喜欢做翻译 高莽先生的笔名众多,不过“乌兰汗”这个名字却称得上大名鼎鼎。记得第一次读到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《人与事》时,译笔的美丽让人惊讶,后来才知道译者“乌兰汗”就是高先生。 从我17岁公开发表第一首翻译作品算起,译龄已有60多年了。但最初,我并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。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东北长大的。面对当时的现实,特别是看到奴相十足的“翻译官”,十分厌恶。我觉得翻译是给别人服务,替统治者做事。 我当时译的是屠格涅夫晚年写的《曾是多么鲜多么美的一些玫瑰》,这首诗的名字我到现在都忘不了,因为它给你带来很多幻想。读这首诗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朦胧的希望在呼唤着自己,感觉挺神秘的。 那个时候,哈尔滨是伪满洲国的一座城市,生活太黑暗了。要想去北京,还得办出国护照。我活得很消沉,看不到自己的前途,也没有革命意识。 1945年8月15日哈尔滨光复,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。我在友协的报社工作,常常翻译些俄苏的诗歌散文,当时用过至少有七、八个笔名,其中一个名字是“何焉”,我是在反问自己:“我不喜欢做翻译,为什么还在做?”1949年初有一天,路过哈尔滨的戈宝权同志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、研究者见见面。那时候,他很有名气,是研究苏联文学的头面人物。 我跟戈宝权说了我不想做翻译的想法。他说那要看是给谁做翻译,翻译的是什么作品。我立刻领悟了,从此,我决心要为人民做翻译,并起笔名“乌兰汗”,即做“红色的人”的意思。 全国都说东北话 高先生受的教育不多,才会有“全国都说东北话”的笑话。现在回想当年的轶事,除了感慨当时信息不畅,更需要注意的是那一代翻译家的起点和生存环境。 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时候,读到俄文版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。这是根据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改编的剧本,它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。你们没法想象我当时的感动。而且,对比之下,更为自己感到惭愧,所以我把它翻译了出来。 1947年,这部话剧被教师联合会剧团选中公演,其中冬妮娅的扮演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孙杰。那时大家都不了解苏联的情况,甚至人物的衣着打扮也都想象不出来。孙杰常常找我了解剧本里的一些问题…… 当时尽管演出条件差,但演出场场爆满。解放初期,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这部戏,用的是我翻译的那个剧本,导演是从苏联回国的孙维世,演员中有大名鼎鼎的金山、张瑞芳等人。剧本里有一些台词是东北话,青艺演出时作了改动,我是在哈尔滨土生土长的,没去过其他地方,以为全国人民说的都是我们那种语言呢。 “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” 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女诗人,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。现在回头看看往事,除了荒谬,还需要一点警惕。 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让我重新认识了苏联诗歌。多少年后,我在一首诗中写过阿赫玛托娃是“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,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”,“背负着沉重的黑色十字,跋涉于凄风苦雨的人世,寒霜打僵了她的心,烈火烧尽了她的诗,她变成了影子,影子也得消逝……”1946年,苏联公布了《联共(布)中央关于<星>和<列宁格勒>杂志的决议》,日丹诺夫为此作了专门的报告,大肆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。那时,我们非常重视苏共的文件。这样一个有关文艺的决议和报告当然要翻译出来,供我国文艺界学习。我译了初稿。翻译这个决议的时候,我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。 这个决议和报告把阿赫玛托娃骂得一塌糊涂,说她是“混合着淫声和祈告的荡妇和尼姑”,等等。我不但翻译了而且还接受了决议的观点。1954年,我随着我国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他们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,和阿赫玛托娃住在同一个旅馆里,如果当时见到她,我一定会以决议和报告的精神来看待她……所幸,我们没有见过面。现在我常常想,那个时候脑子怎么那么简单? 文革后,我想了解阿赫玛托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,为什么要被骂作“荡妇”。在北京图书馆借到西方出版的她的原著,书上还打着“内部参考”的图章。一看才发现,她的诗歌毫无荡妇的影子!特别是读了她的长诗《安魂曲》之后,更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诗人。我翻译了一些她的作品,越来越喜欢。 我觉得我愧对阿赫玛托娃。当年我毕竟翻译过联共(布)不切实际的决议和报告,而且还让好多人都相信了那种极左的看法。后来我专程去过她和左琴科的墓,凭吊这两位作家,也写过文章悼念他们。 “怎么批怎么合适” 经常看到高先生为著名文学家作的画像,这些肖像往往是形神兼似的。有时候不免会觉得高先生其实更应该是一位画家。 解放初期,文艺界挨批的,我大概是第一人,只不过我是“小萝卜头”,不为大家所注意,而且在我之后文艺界又出现了几个“反党集团”大案。 1948年,哈尔滨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了反浪费运动。哈尔滨团市委《学习报》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。我画了7幅反浪费的漫画,刊出了4幅。后来,约我作画的编辑传达上级指示,要我检讨,说有人提出批评,指责我丑化劳动人民,是立场问题,对读者有害等等。 新中国成立后,不知道是谁又把这4幅漫画寄给了创刊不久的《文艺报》,说画有问题。《文艺报》编辑部邀请了在京从事漫画和文艺评论工作的部分同志,讨论分析了我的漫画,然后委托华君武和蔡若虹两位美术界领导同志写批判文章。 华君武在文章中对我充满了关切,文章结尾提醒漫画作者说,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政治、坚持真理,一方面不要怕犯错误而搁笔。但我怕犯错误,搁了笔,决心再不用漫画进行讽刺了,夹着尾巴做人吧。从此,我走上另一条路:只赞美,只歌颂。当时东北开展向苏联学习的运动,我画了一本表现火车司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连环画,出版后我送给华君武同志,以为他会表扬我,没想到他说:“你画的不是连环画,是给鉴定做的插图。”“反浪费漫画事件”之后,每次政治运动都要为此事进行检讨。因为我长在敌伪统治的环境里,在教会学校念书,家里又不是无产阶级,属于怎么批怎么合适的那种人。 华君武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段历史时说,批别人容易,批自己难。有一次我碰到他,他说:“当年我批你,可能扼杀了一个漫画家。”我说:“多亏你批了我,也许挽救了一条命。”因为我了解自己的性格,说话没遮拦,如果没有那段经历,以后的政治运动我不知道会犯什么错误。而且我意志薄弱,如果是突然遭遇到那些猛烈的政治运动,说不定就自绝于人民了。 不一样的翻译理念 高莽先生对翻译的理解无疑是超前的,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体认,《世界文学》为读者带来了更多、更新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。 50年代茅盾先生主持《世界文学》杂志时,我作为翻译陪他会见过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,那个人相当于我国的作协主席。茅盾告诉他说我们要发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。那个人说:“这部作品宣扬个人主义,对青年有毒害,还是不要发表为好。”茅盾表示和他的看法不同。 《世界文学》发表了《老人与海》,几年之后,苏联思想界摆脱了禁锢,也发了这部作品。我当时就想,虽然我们好多东西都学习苏联,总说“苏联是老大哥”,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”,但我们不一定全都不如人家,比如对《老人与海》的看法,茅盾就比他们看得远看得深。 我在《世界文学》工作期间,也尽量介绍外国新的流派,有代表性的新作品。 我翻译了一些作品。有的老翻译家劝我翻译经典的作品,但我不太愿意翻译前人已经翻译过的。第一位优秀译者费的苦心是不容轻视的,而现在有股不正的风气,有的人找出四五个前人的译本,综合一下,就成了自己的作品。 我也不愿意翻译历史已经定位成大作家的作品。我老想跟着时代走,在那些作家没有得到定论的时候,测验我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观察能力,判断这个人有无前途,能否成为大作家,然后把他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。 我没能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什么经验,虽然字数在那摆着,年龄在那摆着,但有什么用呐?不过,像我这样既做翻译又画画,自己还进行创作,并且能得到读者和观众认可,也算是幸运了。 (CSC编辑) |
高莽:游吟于翻译与漫画之间
2006-06-12 6897 0 76
76
评论区(0)
正在加载评论...
相关推荐
-
 设计欣赏
设计欣赏
设计工作室Agency of None--创意设计
2024-04-02 2865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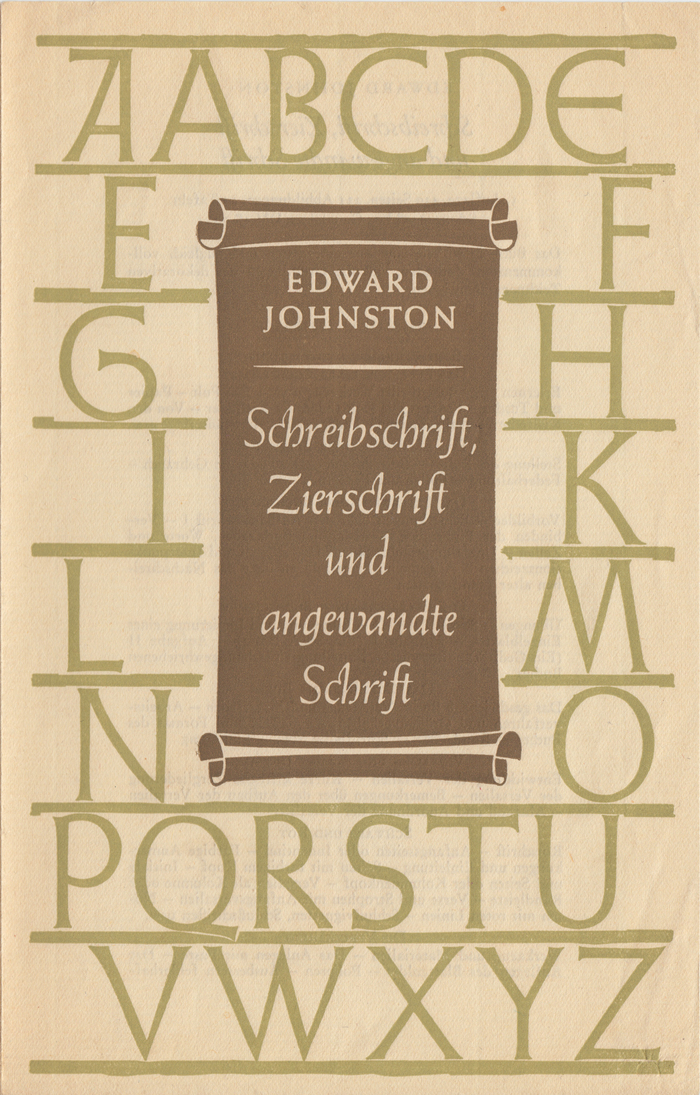 行业资讯
行业资讯
约翰斯顿在皇家艺术学院(Royal Colle
2024-04-02 2672 -
 设计欣赏
设计欣赏
纽约阿卡迪亚当代画廊(Arcadia Conte
2024-04-03 2608 -
 行业资讯
行业资讯
科幻艺术家蒂姆·希尔德布兰特的作品
2024-04-03 2540 -
 行业资讯
行业资讯
艺术家演出海报----设计图
2024-04-03 2529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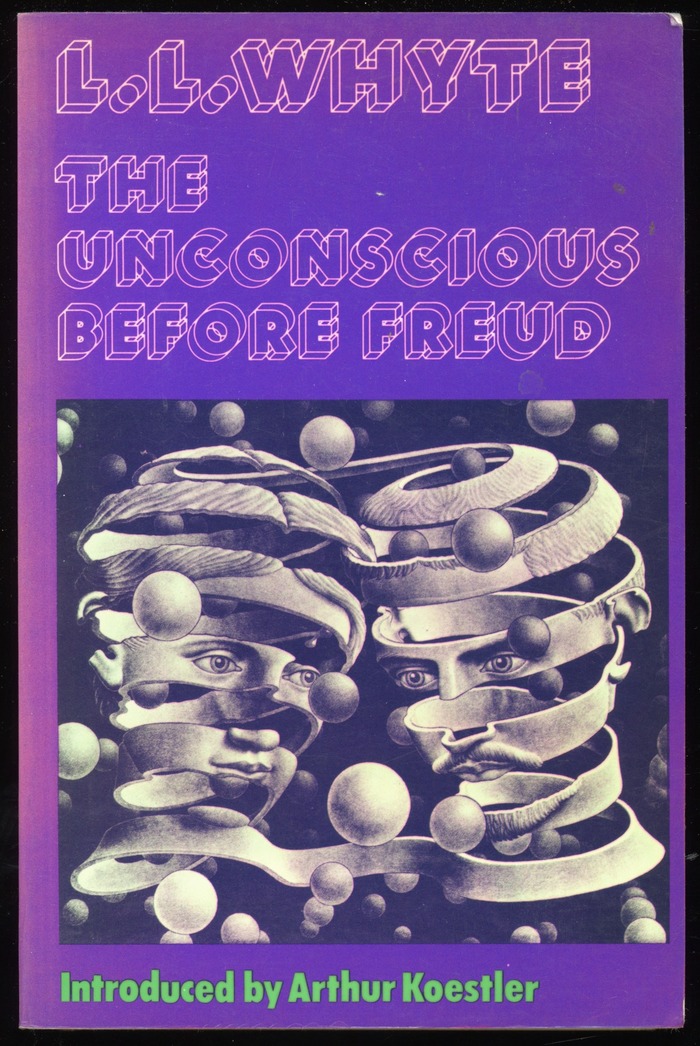 行业资讯
行业资讯
书籍封面---Christof Gassner设计的
2024-04-03 2469 -
 行业资讯
行业资讯
漫画家加文昂丹(Gavin Aung Than)
2024-04-03 2454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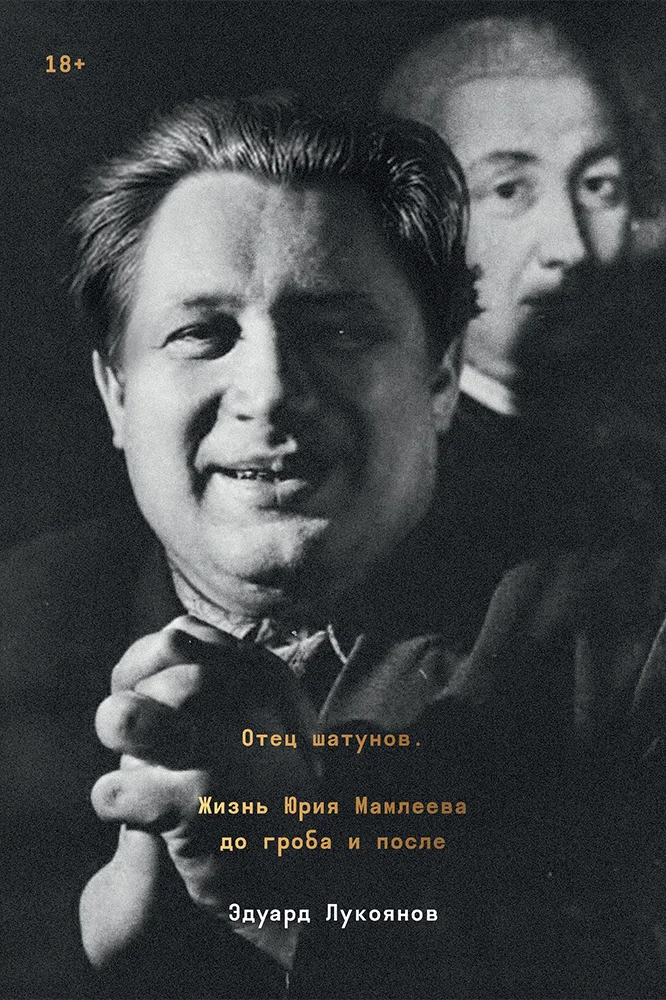 设计欣赏
设计欣赏
爱德华·卢科扬诺夫写的尤里·马姆列
2024-04-02 2287

